明明算是豪言壮语,她却轻拿轻放,理所应当。随口抛出来的一句话,本来也无需过分在意,自信坚定是她的常态。
说话的那一刻,阳光斜照在她侧脸,像一条波光粼粼的河,异常耀目美丽。柯遂又丢了一枚,百无聊赖想,爱上她,同样也如此简单。
从小到大,他对所有人、所有事都是冷眼视之的态度,没有波动,亦无所求,绝对的淡漠。遇见她,才开始有了贪恋——她的所有,他都想要。
所以他不一样,他有很多很多愿望。
硬币全部抛光,水面涟漪散开,渐渐恢复如初。柯黎在一旁看着他,笑着问:“许了什么愿望,二十多个。”
“妈妈。”柯遂唤她,握住她的手。
“愿望说出来就不准了。”
第40章:暗(H)
他们回去又做了一次,他的精液最终还是在她被磨得红彤彤的腿心里射出,混在爱液,温热粘稠。
擦拭干净后,他在她身侧躺下,一只手牢牢揽抱住她。灯已关,如墨夜色漫流。他背后是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,比国内稀疏。
柯黎昏昏欲睡,半梦半醒之间,她隐约察觉他的注视。睁眼,柯遂果然仍在看着她。比暗夜更阒寂、更深幽的,是他的眼睛。
“怎么还不睡?”她问。
“最后一天了。”他说着,手指缓慢在她椎骨挪移,沿寸寸骨节拾阶而上:“想多看看你。”
“回去也能见面。”她柔声说:“我只是出差几天。”
柯遂摇摇头:“不一样。”又凑过来,在她耳畔说:“我要出国了,你不会让我经常回来,也不会再让我这样抱你、亲你,不是吗?”
他说的内容很悲伤,但声音很平淡,像早已接受这个事实。
柯黎胸口一闷,沉重情绪滞在喉间,无法排遣。
她沉默伸出手,抚摸他的头发,忽然抬起下巴,吻他光洁的额头。
吻渐转向下,描摹他立体的线条,山一样走势险峻。最终,她跌入最柔软的地方——第一次,她主动吻他。
她居于权力高位,不能主动,否则就是引诱。孩子有天真、不知世故作为豁免权。而她什么都明白,那些应该的、不应该的。有意犯罪罪加一等。
可她还是吻他。
手下少年的心跳如擂鼓,重重撞击她的掌心。柯遂收紧手臂,丝绸被下两人赤裸的身躯彻底缠绵在一起。他勤于锻炼,身体没有一丝肉感,纯然的坚实、灼热,摩擦过她的肌肤,情欲盎然。
他翻身压到她身上,被子应声而落,滑到一侧。两人的唇依然相连,他的手伸入她的后脑,轻轻抬起,加重、加深这个吻。舌尖柔慢地在她口中撩拨侵占的同时,下腹欲望早已苏醒,抵在她小腹,愈发坚硬。
她握住那根坚挺,从他灼热的吻中退出,轻喘着说:“今天进来吧。”
“真的吗?”他俯下身,与她对视。
“嗯。”柯黎回望他的眼睛,抚摸他浓密的睫毛:“你不是一直想要吗?”
“难道你不想吗?妈妈。”他反问,伸出手指,轻拂她的鼻尖:“不能总是拿我做借口。”
柯黎不语。他的渴求源于恋母情结,可她的呢?医学和科学没有给她的欲望提供合理的位置,是彻底反常的病态。
她感到痛苦,默默望着他,眼神惶惑。
他察觉,低下头,轻柔地在她脸上啄吻,握住她的手:“是我想要你。”
“是我逼你。”
“你只是因为太爱我了。”他轻轻说。“不要自责,好不好?”
柯黎不出声,静默地拥紧他。
他试图用情欲让她分神,含住她的耳珠,指尖撩动她的尾骨。她最敏感的所在这几天都被他一一发掘,像堤坝上的裂缝,稍稍冲击,便汩汩渗水。
她酥软下来,鼻息轻浅,手臂无力将他攀附。
“舒服吗?”他的手探入她腿心,满意地摸到一手湿滑,就着那些液体轻捻花珠,灵巧挑逗。
“嗯。”她真像融化了,平日的冷硬与倔强消失不见,化作一溪春水,从里到外散发馥郁细香。这样的风情也曾向别的男人流泻吗?他既嫉妒,又痴迷,两根手指滑到阴户内凹陷,慢慢插了进去。
他从不急躁,事先都会规划,妥善而缜密,犹如擅长博弈的棋手。
床上风格亦是如此,尽管充满情欲,又是初次。他依旧慢条斯理,手指在甬道内耐心搜寻,找她的极乐点。
两指因为弹琴伸张,都覆有薄茧。粗糙碾过柔嫩,痛感中有快感。她咬着唇,胸口起伏,用理智调控呼吸。
好不容易平息下来,他的指腹进攻略微发硬的区域:“是这里吗——”
快感汹涌,喘息从咬紧的齿缝唇缝中倾泄,她身体率先作出回答。他心下了然,膝盖顶开她双腿,怕看不清晰,探身去开灯——
“别……”她声音沙哑:“别开灯。”
满室暗昧,仅靠微光照亮。四处漫着黑雾,就像他们的情感,不得一窥天光。他知道,她也知道。
他收回手,重新覆压下来。看不清脸,仅是高大而深浓的阴影。她张开双臂,拥抱这片暗色。
硬如盘石的顶端在缝隙上下求索,她鼻间细细簌簌,发出短促的气声。感受那根东西挤开缝隙,沉重地往里插了进来,寸寸抵开。
他是她生的,器官自然也与她相契,简单插入即有快感。她忽然意识到他没戴套,但无暇顾及,肉碾肉的摩擦带来比平常多得多的刺激。粗大缓慢入侵,犹如分娩时,他也是这样胀满她的甬道。
腿被抬得更高,他一鼓作气尽根埋入,插到最深处。
与她耻骨相抵,彻底嵌合。
浑身战栗,她仿佛沉到这片以他为名的深海底部,被四面八方的水侵袭。她快要窒息,很想流泪——不止因为情欲。
耳边轰鸣,他好像讲了什么,语声湮没在黑暗的潮水。她蹙眉,艰难从喘息里挤出一句“什么?”男孩凑过来,在她耳边又重复一遍,声音清晰而笃定。
他说我爱你。
真的。
第41章:授(H)
胀大的肉棒直捣花心,本该开始挺动,他却停住,压在她身上,呼吸极其紊乱。
柯黎发觉不对劲,抚摸他汗湿的脸:“怎么了宝贝?”
“有点想射。”其实是很想射,凹凸不平的褶皱紧勒住未经人事的性器,波涌着要将他榨干。柯遂有些懊恼,深深吐出一口气,慢慢拔出来。
“想射就射。”她尝试安抚:“第一次都是这样,贺昀当时也……”
“妈妈。”他打断她,手指捏着她下巴,促她跟他对视。眼睛融在夜色里,沉沉盯着她:“不要提别人。”
他偶尔会露出仅属于男性的一面,极富侵略性,总让她思维迟滞半拍,吃力地将这一面与平日联系。
走神之际,那根东西又插了回来,强烈的堵胀感再度来袭,不止是阴道,好似整个身体都被他充盈、填满。她皱眉,腰肢不自觉向后摆动,却被他环住,用力拽了回来,胀硬顶端再次碾滚过深处软肉。
他就这样将她禁锢在怀中,缓过射意后,不紧不慢在她腿间进出,顶得她身躯一挺一挺,握着床单的手时而攥紧,时而松开。
终究忍不住,她仰头张唇,无声对着黑暗喘息。
夜色裹住他们性事视觉的一部分,但听觉——他胯骨与她臀部相撞的肉体拍打声,性器相互摩擦的滋滋水声,以及两人呼吸不畅的喘息,无一遗漏从中漫溢出来。
但于他而言,这仍然不够。他拈起她遮挡眉眼的几缕发丝,别在耳边,捧起她的脸,轻柔哄她:“妈妈,看这里,看着……”
她目光移到身下,臀部被他高高抬起,腰肢悬空,他几乎半骑在她身上。粗长的阴茎因为逆光,仅是黑魆魆的阴影,倾斜着捣入她下体。
她想转开,但他的手纹丝不动。她用手挡住,但被他桎梏手腕。
柯黎有些恼怒,声音变得严厉:“柯遂……”
趁她说话,那根巨物又顶入花心。酸麻感如电流攀爬向上,她浑身绷紧,半截声音变成压抑短促的呻吟,极其妩媚。
“是这个地方生下的我吗?”他捏着两瓣臀部,无休止地挺身打桩,精囊无间断拍打肉穴边缘,声响湿腻而淫靡。
“嗯。”她挣扎在情欲洪潮中,反复没顶,无意识答复他。
“那我又回来了,妈妈。”他俯下身,边亲吻她的耳廓,边喃喃,语气迷乱中,透着一丝平静的疯狂:“我又变回你身体的一部分。”
听清楚他的话,柯黎恍然心惊。手被他带着,摸到两人紧密相嵌的交合处。湿滑爱液犹如粘稠的融糖,洇入她颤抖的手掌。
他毫不避讳两人乱伦的事实,明明白白告诉她,他们情人姿势下的实质。
可是为什么,她的身体愈发有感觉。阴蒂膨大,硬硬地抵在他的耻部。他伸出手,指腹两面夹紧花核,用力揉捏。一股难耐的瘙痒和酥麻随他手指蔓延到甬道每一处,更加裹紧了他。
他却用力拔出来,留她吊在原处不上不下,腿根发颤,水液汩汩涌出。想要但说不出口,最是虚无软弱的那刻,他又骤然插入泥泞不堪的逼穴。水液飞溅,撞击变得激烈,带来无限的快感,轰然冲破理智,把那些伦理纲常道德律令都荡得稀碎。
她开始挺腰迎合,双腿缠住他起伏入侵的窄腰,手指攀上他平阔的脊背。呻吟声不受控越来越大,也越来越娇柔,染上些许哭腔。
……不行了。她想,快高潮了。可这不能,至少不应该,用生出他的产道感受欲仙欲死的愉悦,这是被禁止的快感。
但欲望全不受阻,身体不听从她意志摆布。来势汹汹的几击下穴肉霎时缩紧,层层迭迭的软肉被阴茎的形状与盘旋其上的青筋血管塑形,她的喘息戛然而止,被下体汁水细微的喷发声取代。
他骤然被绞紧,发出一声闷喘。温润的嗓音变得混浊嘶哑,精关冲破前抱紧她,压着她无力大张的双腿用力再顶数十抽,撞进花心深处,一遍又一遍告白:“妈妈,我爱你。”
“……我是你的,你也是我的,只能是我的。”
这几句重迭反复,犹如催眠。她眼中泪意闪烁,感到身体出现内爆,禁忌随他精液在子宫迸发的那一刻灰飞烟灭。她像陷在蛛网的蝴蝶,濒死挣动了一下,又被他掰开双腿,腰腹密不可分贴覆上来,以一种镇压的姿势,按着她授精。
他要用最暴烈与最缠绵的方式叫她记住这感受——他依然在她体内,不论出生前还是出生后,不论怀孕还是做爱,他依然扎根在她身体,谁也不能轻易拔出。
就是她也不能。
粘稠白精随堵塞消失涌出体外,流满她的花心。他搂紧她洇出薄汗的腰肢,舌尖滑入她唇间,缠住她无力的舌头,色情又温柔地吮吸。温凉水意覆满两人全身,于夜中透亮反光,她恍惚觉得,这是他出生时裹住身体的羊水。
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她察觉他紧贴小腹的阴茎又硬了起来,坚挺的龟头往下挑开缝隙,嵌到肉穴又待再入。她摇头,往下握着那根跃跃欲试的阴茎,低声道:“戴套。”
“你想让我怀孕吗?”
“不会怀孕。”他凑近她,两人发丝纠缠,汗水与气息交融中,他亲吻她的脸:“我怎么可能让你有第二个孩子,只能有我一个。”
柯黎怔住,她震惊望向他:“你……”
“嗯,我做过手术了。”柯遂轻描淡写。
“太不慎重了。”她拧紧眉头:“这不是儿戏,柯遂。”
“这根东西除了和你做爱以外没有任何意义。”他微笑,轻巧地说:“它是你创造的,所以只能用来……”
“进入你。”
他理所应当把自己全身上下都归属于她,岂止是没有断奶,他完全还把自己当做她腹中的胎儿。
如此极端、如此畸形的爱恋令柯黎浑身发颤,可她别无选择——是她先放他进来,谁料一发不可收拾。膝盖再次被他抬起,他腰身一沉,烙铁般的肉棒旋即深深插入体内,掠夺她的全部。
第42章:溺(H)
这一晚数不清他吻她多少次,做了多少次,晕过去——或者说,睡过去前他们仍然在接吻,她第一次知道吻太久了舌头也会酸,明明平常说话频繁使用,偏偏在和他百般缠绕之后疲于再动弹。他终于恋恋不舍从她口中撤出舌尖,带出牵连的银丝。阴茎仍停在她体内一动不动。
第二天七点,这边教堂准时敲钟,晨光与祷歌漂浮,涌入窗口。
柯黎昏昏沉沉起床,她已经形成一套固定的起床程序,一睁眼就下床,绝不多睡。
起来时下体像拔出来什么,满满当当堵在里面的液体刹那间涌出,染白腿根。意识到前她一只脚已经踏在地上,却蓦然酸软,砰的一声坐回床。
躺在旁边的柯遂被吵醒,撑坐起身。他骨架修长舒展,薄薄覆层肌肉,晨光下是冷玉的质地,线条分明但不过分强壮,极具美感。唯独狰狞难看的那根东西正因晨勃高竖,跟她下体一样,同样黏黏糊糊,沾满各色液体。
她忽然发现,塞了一晚那东西是什么。
腰腿酸麻,头更是如同宿醉以后,隐隐发昏。她按按额角,身后忽然扬来两只有力的手臂,将她抱入怀中。柯黎精疲力竭,靠到他肩膀。
他的气味很好闻,温和的皂感,透着少年的清爽。被他拥抱是一种享受,于她而言。
“妈妈,有没有不舒服?”柯遂低声询问,垂眸下看。女人花户像被捣烂的浆果,裂缝殷红,四溢着精浆。
他深深盯着,将这副彻底占有她的淫靡景象刻入脑海,又伸出手指,缓缓插入柔嫩花心,带出更多液体,气味浓郁。
一面排精,他悄无声息拨弄她的敏感,试探碾压。柯黎眉心蹙紧,双颊潮红,唇间泄出细碎轻吟。
见她这副情态,他不禁垂首,亲吻她的脖颈,一只手握住一边乳房,轻缓揉捏。
“还做吗?”她问,语气犹带倦意。
“可以吗?”他低声问:“妈妈,你要不要睡一觉?”
“飞机上睡。”
他听出她的纵容,更搂紧她,手指再递入一根。这一次明目张胆起来,双指直直插进肉丘,旋着在湿滑甬道里捣弄。
黏白液体越流越多,不知道射了多少。他轻啮她的耳垂,问:“你会让别人射在里面吗?”
“不会。”她把手搭在他正在插穴的手臂上,喘息愈发急促:“……当初为了怀孕,才让你爸爸弄在里面。”
他瞬间抓住普遍性:“那你内射都是为了我。”
她想否认,又无从辩驳,最终只能低低嗯一声。
男孩子的占有欲被满足,亲亲她的脸颊。磨蹭在她臀缝的粗大阴茎往前一挺,被他握住对准穴口,又待再入。
“等一下。”她伸手挡住那物事,不忘提醒:“去洗澡。”
两人一同洗漱,浴室光线撒落在他赤裸的脊背,极其柔和。她瞥一眼,看见上面赫然一道深长的疤痕。
“这里怎么回事?”她伸手抚摸,动作很轻,仿佛他依然会觉得疼。
“小时候不小心摔到了。”柯遂侧过身,没让她继续看:“没什么,已经好了。”
“以后要小心。”她叮嘱:“尤其你一个人在国外。”
“妈妈在我这么大的时候不也独自在国外吗?”他说:“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”
柯黎讶然,她没和他说过过去:“你知道。”
“嗯。”柯遂点头:“我找了很多资料,想了解你以前是怎样的。”
柯黎顿住,抬手揉了揉他的头:“乖。”
语言和动作都很温馨,如果忽略他们正赤身裸体,做爱后并且即将继续做爱的话。他们关系早就变形扭曲了,母子与情人的迭加态——上一刻还是谆谆教导的母亲,下一刻他们已经挪移到淋浴间,水围成雨幕。他抱着她,两条腿都摁在朦胧玻璃上,挺身而入。
水丝如雾,漂浮在四周。肉身交缠,像两尾白鱼,时隐时现。她饱受煎熬,身体内外各处敏感点都遭他占据蹂躏,被顶起又坠落的身躯一直在颤。
性欲高涌的少年腰臀死死嵌在她腿间,盘石般发力坚硬,挺动入侵,低沉的喘声和她的呻吟穿透了水雾。
最后她的腰酸到无力再挺直,他们又到浴缸。水。无止境的水。像圣地,亦是水牢。沉沦从心理变作现实,他的手拂过她湿漉漉的乌发,轻柔地吻她鬓角和唇。
视野逼仄,她只能看见他低垂的浓长睫毛,被水染成漆黑一抹,忍不住摸了摸。他抬眼看她,目光清澈而温润。
“妈妈爱我吗?”他俯下身,吻她的唇,再次开始动作,翻出一池波澜。
“嗯。”她感受他此刻温柔如水的进入。水里他的身躯变得非常轻盈,即便压下来,偶尔会飘荡离开,云一般时聚时散:“但不是那种爱。”她执拗不肯承认。
“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?”他握住她绵软的腰肢,一气插到最深,像要钻到她最柔软最真实的那处,撬开在光明下:“不是那种爱,又是什么?”
像触碰未愈合的创口,她下意识回避,偏过头去。他的动作却陡然激烈,她被幽禁在水和他又急又热的情欲中,难捱地低吟。
下巴被他抬起,小舌躲闪不及,又被他挑弄吸吮。水压得她喘不过气,热气熏然,她同时感到无限的痛苦,与无限的愉悦。
再这样下去真的会死,各种意义上的死——真应了她的谶,高潮时两人全无防备,没到水底。挣扎之际性器依然死死纠缠,共同爆发。水灌入眼耳鼻舌,隔绝一切色声香味触法。无光的暗流中,她死死抱紧他,可他不是浮木,只能偕她一同溺亡。
残存一丝理智,柯遂撑住缸底,捞着她的腰,用力起身。香甜空气涌入鼻间,两人咳嗽半天,终于缓过来。
他抱住她,轻抚她颤抖的脊背,抹去冷汗与水,垂头问:“妈妈,如果我们淹死了,会不会上新闻。”
柯黎靠在浴缸边沿,始终闭着眼睛,缓缓喘气,没有看他一眼。
“你是真的疯了。”良久,她说。
 神回复
神回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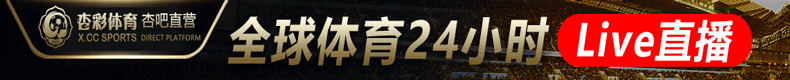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